注册新用户
- 登录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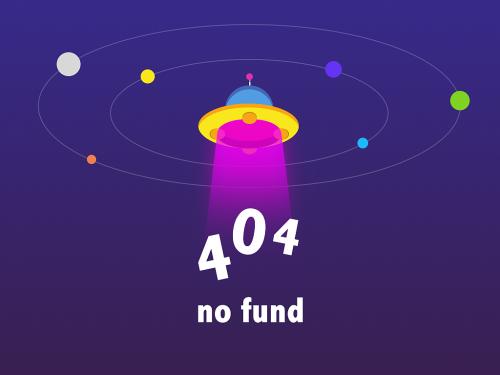
注册新用户
修改密码
我年轻的时候,也曾着迷过“意识流”“先锋派”之类的写作,并以此类形式写过几篇小说。但很快,我就对这类形式不感兴趣了,我开始喜欢一些老作家的作品,比如汪曾祺、林斤澜、张中行等等。我喜欢他们的老而率真,体露真常。我不喜欢那些赶潮的作家,这类作品生命不会太长。我觉得,一个成熟的作家,在写作上应该做到“从心所欲,不逾矩。”
张中行老先生是我最敬重的老作家之一。老先生在散文杂文上“暴得大名”,已经是80岁左右了,比汪曾祺先生“暴得大名”,年岁上还要晚大约20年。张老先生在解放前主要是当教师,还编过杂志。解放后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辑,主要工作是编课本,编古文读本等等,名气并不怎么大,但圈内的人都知道他学养深厚。季羡林曾评价张中行“学富五车,腹笥丰盈”,并称他是“高人、逸人、至人、超人”。我想,张老先生平生潜心治学,淡泊名利,生活简朴,中和顺生,确实担得起季羡林先生的评价。启功先生则说张中行先生是“说现象不拘于一点,谈学理不妄自尊大”,这都是中肯之言。上世纪末,张中行、季羡林、金克木被誉名“燕园三老”。
张中行之“暴得大名”,是在他发表并出版了《负暄琐话》《负暄续话》《负暄三话》《月旦集》《禅外说禅》《顺生论》等著作之后,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一阵旋风,人称“文坛老旋风”,他撰写的文章,一度被称作“新世说新语”。其中,《顺生论》耗老先生心血最多,也是他的代表作。启功先生对他的评价是:“散文杂文,不衫不履,如独树出林,俯视风云。”尽管博得如此大名,老先生依然故我,照旧穿他的老棉袄,旧布鞋,依然吃他喜欢的老面烧饼,喝他喜欢的普通二锅头,80多岁了还挤公共汽车。他常年寓居在女儿的家中,直到86岁那年,才分到一套平常的三居室,家中没有搞装修,保留着水泥地面,家中设置极为简约,书房里也只有两个书柜,一张书桌和一些清玩,其中以石头居多。张老先生喜欢石头,大约是喜欢“石不能言最可人”吧。他为自己的居室起了一个名,叫“都市柴门”。
我读过张中行老先生的绝大部分著作,切实感受到老先生学问深广,不仅古文极好,儒释道三家皆通,对西方哲学亦谙熟,在书法上也很有造诣。我曾在一份报纸上(什么报我忘了)看到,启功先生曾邀请张中行先生,想两人一块儿办个书法展,,但张中行先生婉拒了,他说他的字写得不好,这也反映出老先生的谦逊和虚怀。
说到书法,我和张老先生还有一点小机缘——1997年,我在《广州文艺》杂志做编辑,主编要我约一些名家稿,于是我就冒昧地给张老先生写了封约稿信,并在信中更冒昧地表示想要求他一幅字。信寄出后不到一个月,回信到了,我看信挺厚,拿起信,感到信封里面软绵绵的,心头不由一喜——里面必有字幅无疑!我小心翼翼地拆开信,果然里面有一幅字。我急忙展开来看,这一看我愣了半天——字的好不用说,是书写的内容让我愣住了,字幅的内容是:“思君令人老 岁月忽已晚 古诗十九首句每喜读之 程鹰先生正腕 丁丑冬张中行”。这下把我弄糊涂了,因为“思君令人老,岁月忽已晚”是《古诗十九首·行行复行行》里的诗句,是一位思妇写给经年不见的远方丈夫的,张老先生何以将这样的诗句题写给了我?他明明知道我是一位男编辑。还有,张老先生说他“每喜读之”,这又让我纳闷,何以一位88岁的学者,哲学家,古文专家、散文大家,会对两句古代思妇写的诗“每喜读之”呢?真是“逸人”之举,常人难解。
随字幅还附了一短函:“上月末大札拜收。承奖掖,至感且愧。我不能书,且近来目力甚坏,勉成一幅奉上报命。手头无文稿,暂不能应命。匆匆,颂:编安。张中行拜97.11.22。”
我把字幅和短函反复看,脑海里忽然浮现出儒家的“温柔敦厚”这四个字来。从字幅的内容里,我看到了老先生的温柔;从短函的内容里,我看到了老先生的敦厚。
我和张老先生缘悭一面,1998年国庆期间,我出差去北京,想见老先生,但我没有老先生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,只能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去问,出版社的人告诉我:老先生这段时间不在京,他想老家了,回家乡去了。
老先生于2006年2月24日在解放军305医院安然辞世,享年98岁,身后没有给后代留下任何遗产。
许多年又过去了,老先生给我写的字幅,一直挂在我的书房里。现今,我竟也会常常进入“思君令人老,岁月忽已晚”的境界。
编辑:文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