注册新用户
- 登录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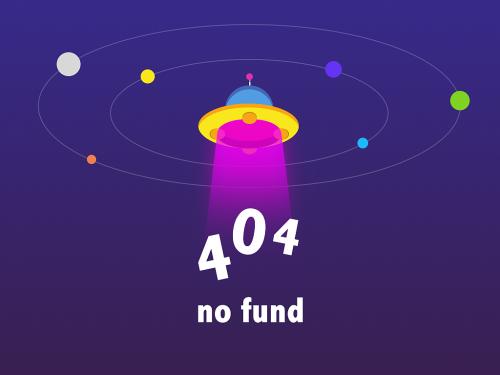
注册新用户
修改密码
我们家第一间屋的建成,是大哥六岁那年。从前年冬天,父亲开始伐树,父亲把树去了枝条,放进塘中,浸泡上一个冬季,一棵树就蜕变成一根木料了。就像锻造一个愣头青的小伙,挤压掉身上空泛的锐气,便只剩下实实在在的瓤。
备下几根木料,房梁,顶撑就有了。剩下的多是卖力气就可以克服完成的工序。从塘子里挖出淤泥,拌进稻草,这便是四堵墙的材料。而用来做顶的泥,必定是淤泥下面一层,结实一些,踩在脚下肉筋筋的,掺上稻草,再掺上灶膛里新鲜的青灰,搅拌均匀,放进槽子里,拿来推稻子的长条木锨,来回推拉,直至平展,以一个固定的厚度。有了这,房顶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一半。剩下的是在它下面放木料作房梁,在它的上面铺上稻草。一座茅草房便敦敦实实地大功告成。
凡事说起来容易,泥苇子的厚薄,稻草的匀实。放屋顶上的,需铺出层次,稻草之间要扣合好,一层一层之间,不能脱节落下空挡,要不然遇上阴天下雨,下雪,刮风打雷的天气,特别是夏天里一股又一股的台风侵袭,立于房顶的稻草哪里能经得住啊!
父母结婚时的屋,是借来的。那屋比父母后来盖的屋要好一些。墙是黑砖,显得粗实,功夫不细,而且比后来的红砖要显大,瓷实,坚沉。那至少是砖啊!是砖就有几分不一般的贵气。房顶也不是稻草,而是黑瓦,一片一片呈弧形,像两个手掌贴在一起,打成一个窝的形状,接近一个菱形的一半。现在想想,那不就是徽派建筑顶上的瓦砾吗?
新建成的房子还冒着水汽,湿漉漉的味道弥散在草屋内。父母亲早早地搬进了自己家的屋里。那可是自己家啊!一辈子头一回有了自己的屋。那感觉迫不及待,而又迫在眉睫。住进自己的屋,所有的感觉都不一样了,那是真正当家做主的感觉。
只是老天有时候偏偏喜欢跟穷人开玩笑,不管这玩笑的大小。也就是那一年,经过一个夏季的暴晒,有了干气的房子,被大哥不小心一把火烧了。等父母亲赶回来,新屋只剩下四堵墙垣孤零零地站在风口。看着残垣断壁,父母亲的心该是怎样破碎。
第二年,我出生后,父母亲又盖了他们生命中第二次屋。原路返回一遍,不用再绕弯路了,比第一次省劲了许多。只可惜,这个屋也没能留住。当年,来河决堤,也就是家乡人说的破圩。当涛涛洪水如下山猛兽,自上而下蜂蛹而来,家乡人立即就如同残兵败将,一路丢盔卸甲,纷纷奔向大坝上。洪水冲破洞穴,势如破竹,如万马狂奔,一眨眼工夫,田地没了,房子没了。到处都是白茫茫的洪水,别说我们家的屋了,村里所有茅草屋,土墙全部坍塌,硬泥块在涛涛洪水之中,即刻现行,坍成一堆泥。
好在那一年,遭遇洪水,国家有专项拨款,对所有受灾户都给予了资金上的扶持。父母亲终于又建了第三次屋。虽然只有一人来高,锅屋住房都在一间,对于父母亲来说,也已经是莫大的安慰莫大的满足了。
这间屋,在我十岁之前变成了家里的锅屋,专意留作烧饭,随着日子一天天好转,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,每一户人家除了自留地,每个人都按人头分到了土地。有了钱的父母亲,面对着一天天长大的四个孩子,果断决定再盖屋。于是,在锅屋旁,父母亲又建了三间瓦房。中间的一间是堂屋,一边的屋作为大哥、二哥的房间,我和姐在父母亲的床后面铺了一张床。母亲用蚊帐把他们的床与我和姐的床隔开。
在我上初中那年,1985年,我们家第五次建屋。这一次非常正式,也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以及精力。父母亲为此,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准备,计划,分工,一点点置办所需的工料。从红砖,石头,沙子,水泥到白石灰。当时建的是四间砖砌的大瓦房,这四间大瓦房,后来竟成了父亲的绝唱。父亲在自己亲手建造的屋里离开了这个尘世。
那时,我们家也已在相邻的镇上买了另一处屋,是二哥坚持着买的。买时,父亲还在。父亲看着街上的屋,又看看乡里的屋,五味杂陈,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但父亲的心里其实是高兴的,一辈子单枪匹马,没有兄弟姐妹的父亲,怎么也不会想到,后来,自己家竟然在镇上也有了自己的屋。
如今,那两间屋,在两个哥哥的手里,早已变成了上上下下有十来间的楼房。只是那些屋多数时候是空着的,只有大哥大嫂守着屋子,做一些农副产品生意,以维持生活。有屋就有家,有家,就是牵系,孩子们就像燕子,一只只从远方飞回来。叽叽喳喳的孩子们,使得偌大的屋的鲜凌凌的气息直往外冒。
编辑:文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