注册新用户
- 登录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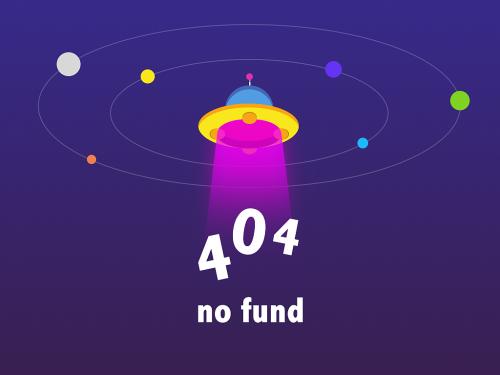
注册新用户
修改密码
我家位于黄山太平湖的一角,冬天早上,湖面飘飘缈缈凝着一团白雾,雾气遮住木船,遮住对岸的山峦,沉沉地压在水上。九十点钟,太阳出来,橙红色的光线洒进水里,缠绕着将散的残雾。半晌,雾气散尽,水面又平静碧绿,微波荡漾。逢到大雪天,就真是“上下一白”了。
傍晚,天阴沉,落雪的几率最大。我坐在屋里,照着暖黄的灯光烤火,看窗外绵绵地洒下雪来,软软地,有弹性。不出意外,第二天清早,不必开灯,就能望见窗外的瓦片上映出白色来。大雪静静地下了一夜,层层叠叠的瓦片上铺满了雪,凸起的地方像一个个小馒头。树桠子上也是雪,房檐下结了大大小小一排冰溜子,我觉得那大冰溜子长得很胖,很想摘来当玩具。雪或许还在下,父亲早早起床,拿一个大铁锹四处铲,给前门后院铲出一条条路。我就跟着看雪地里的脚印,鸡脚印很好看,细细小小,踩得很浅,像一棵树干分出桠来,我觉得这样晶莹的脚印若是出现在画家的笔下,也是一种趣味。人的脚印很深,大小不一。我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,雪天走路,喜欢走在人家留下的脚印上,恨不能严丝合缝地贴上去。
人们常说:“下雪不冷化雪冷。”三两天后,太阳出来,各家各户的房檐上都淅淅沥沥地滴水。院子里积了小水洼,跑快了,要溅湿裤脚。没有化尽的雪堆越来越小,也越来越黑。虽有太阳,温度却是很低的,冷得人骨子里发寒,似乎动一下都会咯吱咯吱地响。
雪化尽后,母亲坐在墙角下打各种颜色的毛线鞋,我靠在椅上看书,看汪曾祺先生的《新校舍》,遇到有趣之处,我就读给母亲听。“……也有根本不是联大的,却在宿舍里住了几年。有一个青年小说家曹卣——他很年轻就在《文学》这样的大杂志上发表过小说——他是同济大学的,却住在二十五号宿舍。也不到同济上课,整天在二十五号写小说。”在联大,像这样的文人趣事不少,母亲听得咯咯直笑。我喜欢这样无风的下午,太阳旋转,一晃就过去了。
在南方过冬,火桶是不能少的,太阳一落山,就必得烘火。我的北方同学不知道火桶是什么,故而惊讶。以前,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大脸盆,里面放实了灶灰。父亲每早都会在盆里放上一小堆烧着的炭,盖上灰,放进火桶里。人坐在火桶沿,脚落在铁盖上,下面则是一盆炭火,其乐融融。
吃晚饭的时候,桌下是通红的炭火,桌上是滚烫的家常菜。雪菜炖豆腐吃得最多,且是放在炉子上边煮边吃。年前,母亲都要洗很多新鲜大白菜,搓揉、撒盐、盖石,腌上一缸。肉片入锅后滚油爆炒,酱醋去涩添色,放入豆腐和腌白菜同炒,着辣椒干增味,微煮收水即可。吃酸菜豆腐的时候,母亲常提道,她小时候过年,能吃到这样的酸菜豆腐就是幸福的事。母亲是一个念旧的人,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唱老歌,声音清亮。她还想念过去牛奶糖和饼干的味道,现在,很难找到那样的味道了。萝卜炖肉是父亲喜欢的。肉和萝卜都炖得入口即化,肉有萝卜的清香,萝卜有肉的厚重。一锅萝卜炖肉被炭火煮得咕咚咕咚响,锅底下冒出泡来,催你赶紧地去吃它。
秋天收下的花生,晒干封好,留到冬天,可炖可炒。炒花生得用小火,慢慢来,炒到香气溢出,尝一个,熟了,起锅。刚起锅的炒花生不脆,要等晾冷了才好。剥开壳,皮成了深红色,花生是黄褐色的,吃一口,有炭火带来的香味,还有点儿焦香。一整个冬天,酸菜豆腐、萝卜炖肉、炒花生,满足了我一大部分的口味。
火桶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处,比如烤红薯:将红薯埋进炭火里,盖上灰,大约半个多小时,闻到香味就熟了;冬天洗完澡,衣服穿在身上冰凉,得先放在火桶上烘暖;除夕那天,家家做年夜饭,菜早早做好,一会儿就搁冷了,巧妇们就把菜放进火桶里保温……如今,木炭难得,桶匠已不多见,电火桶成了新宠儿。我用不惯电火桶,那么冷的天,手脚都冻冰了,窝进去半天,也只有半吊子的温度,不是太冷就是太热,没有一点“中庸”的精神。
一入冬,母亲即使窝在火桶里,也得戴上一顶高高的毛线帽,还有口罩。她头冷,脸也冰,鼻子总是红彤彤的,像个胡萝卜。母亲说:她打小就怕冷,一到冬天,河水都冰冻了,孩子们背着花花绿绿的书包,跑在冰河上,叽叽喳喳,赶集似地去上学。风大,手也冰凉,母亲经常被冻得大哭,外公无法,只好送了一只火桶去学校,母亲这才不哭。
如今,每年冬天,太平湖的水面上仍有白雾,母亲还在做着雪菜炖豆腐。但是,冬天的味道就像这些年的雪花一样越来越少、越来越淡,越来越让人记忆犹新。
编辑:文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