注册新用户
- 登录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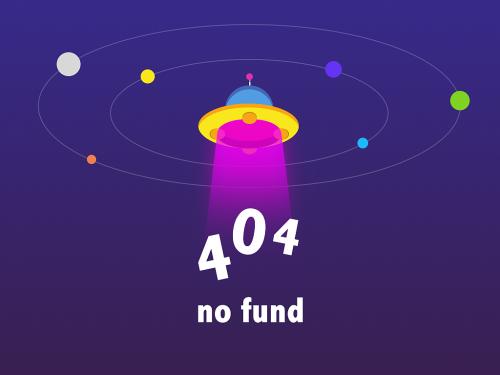
注册新用户
修改密码
年轻的时候,我请著名书法家、篆刻家石开先生为我的书房题了一个匾,曰:晓梦屋。不用说大家也知道,这是出自“庄生晓梦迷蝴蝶”一句。记得当时我和石开先生通长途电话,请他为我题写书房名,他问我:什么斋号?我一愣——因为我没想过,随即脱口而出:晓梦屋——因为当年长途话费很贵,由不得我多想。事后想来,我这个晓梦屋的急出,大约还是潜意识中受了李叔同的书房名“小迷楼”的影响。
石开先生的题字寄来后,我一看,字太大了,而书房太小,无法挂在书房的门楣上以显斯文,只好将斯文收藏起来。几年前换了个大一些的屋子,妻子把最大的房间给我作书房,但石开先生的字仍是嫌大,于是还得将斯文继续收藏起来。
我是从小就酷爱看书的,小学时即开始学写作,故而我对书房一直是很向往的。我没有“坐拥书城”那么大的气派,只要有一间房让我摆放我的书,让我能够在里面清静地读和写,就足够了。
我对我现在的书房很满意,尽管它只能摆放我三分之二的书籍,但对于清贫的我来说,已经很惬意了。我每天绝大部分时间,都是在书房里,读书、写作、学书法、练古琴、打坐等等。我们家所有与艺术有关的东西,统统都放在我的书房里,比如文玩、字画、埙、古琴、吉他、小提琴什么的……对了,还有从各地捡来的石头。书房里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,我就不想出去玩了,我每天在客厅、厨房、阳台上呆的时间,加起来可能不足一个半小时。
不知为什么,只要呆在书房里,我就身体舒泰,神清气爽,感到很自在,很悠然。我可以在这片天地里做我的事,即便什么都不做,我也可以随意浮想,作我的“逍遥游”。其实,在书房里随意神游,是一件很美妙的事。游到神飞时,如列子御风;游到无心处,似颜回坐忘。
当然,我在书房里更多的时间是在读书,做笔记,否则书房就不是书房,而成蜃楼了。我的藏书很杂,所以我的阅读也就很杂,这缘于我的爱好过于广泛,难以专精。但我以为,作为一个作家,爱好广泛不是一件坏事,恍惚记得林语堂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。治学则不同,需要专精,曾国藩就反复叮嘱他的儿子曾纪泽读书要专精。
因为读书杂,所以我的书房就显得乱。我在读书时,常常会读到某一节,忽然联想到另一本书里说的话,于是就赶紧找出那本书翻阅,翻阅中碰到某句话,又会想到别的书里的内容,于是又从书架上取出另一部书……如此链接牵扯,结果常常是我开头读的是萨特的《文字生涯》,两三个小时后,我手中捧的竟然是一本《天工开物》,而书桌上摊满了翻开的书。我不知道这样的阅读是不是一种坏习惯,不符合读书法。反正我自己喜欢这样读,像漫游一样,可以让感知汇成片。但也正因如此,我的书房就显得很乱,到处都是书,而且有不少书是读到一半的,折叠在那儿,仿佛被打入冷宫似的。但愿这些书不要有怨气,我迟早会把它们读完的。我自己所藏的书,我基本上翻完了,但实话实说,我认真仔细读过的书,大概不会超过三百本。
书房是我的生活安心处,也是我的精神自在天,所以我不太喜欢去别的地方,趣味使然,莫可奈何。有人认为我清高,真冤。
我妻子为了整洁,常趁我不在的时候整理我的书房,这使我有点哭笑不得,因为我的书虽然貌似混乱,但我心中知道它们在哪个地方,故“处处不在处处在”,经我妻子一整理之后,就成了“众里寻他千”了。
我有不少名家给我的字幅和画,因为墙面大都被书柜占据了,我只能张挂两幅字,一幅是汪曾祺先生的,内文是:“我与我周旋久,宁作我”;一幅是张中行的,内文是:“思君令人老,岁月忽已晚。古诗十九首句每喜读之”。我很喜欢这两幅字,每看到它们,心中既清凉又有暖意。
我认为一个家中,有三房最重要:即厨房、卧房和书房。盖厨房能厚脾胃充体力,卧房能安心神补精力,而书房,则可与天地精神相往来。
编辑:文潮